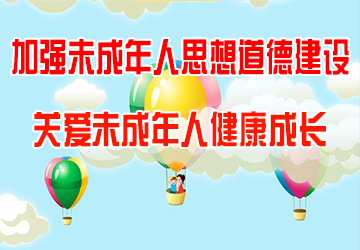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,一份证据竟然在两起案件中使用,特别是二审法院的法官系同一人。这样的判决案例发生在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。该案件虽已走完了所有的法律程序,但当事人苏先生却对此案的判决有自己的看法。他认为,法官尤其是二审法官杨某有渎职嫌疑,遂向媒体反映了这起特殊的案例。
苏先生因借高利贷逾期被起诉
2015年6月18日,苏先生与袁某(女)签订借款合同,借款金额275万元,还款时间也是2015年6月18日,借款利息约定:自支用借款之日起,按实际支用数计算利息,借期内月利率为2.5%、服务费2%,利息及服务费按月支付等。因苏先生未能按时还款,袁某起诉到甘井子区人民法院,要求苏先生偿还借款本金275万元及利息。苏先生答辩称275万元并非借款本金,借款数额并非实际发生的借款金额,而是借款本金加高利息形成。
袁某方面陈述为,银行转账两笔70万元、19.4万元,替苏先生给付姜某某47.5万元,合计136.9万元;其余的138.1万元是现金给付,为此袁某提供了一份“银行卡业务回单”,列明了15笔款项,从2011年8月15日至2014年8月6日,其中现金取款(含转账取款)12项,合计金额188.8万元,用于证明现金出借给苏先生,从而形成了275万元借款的合同,并一直确认该275万元中不含有利息,均是实际的借款本金。
现金取款188.8万元这一证件曾被袁某使用过
苏先生的律师经过查询得知,袁某之前和于某某也有一起的民间借贷案件,其卷宗即甘井子区人民法院(2015)甘民初字第49号、大连市中院(2015)大民一终字01246号,袁某和于某某签订借款合同确定的借款金额300万元,袁某通过银行转账、支票给付于某某135.9万元,余下借款通过现金形式陆续给付于某某。袁某并提供一份《借款明细表》,证明自2011年8月15日至2014年8月6日期间,从袁某名下银行账户中提取过现金12笔共188.8万元,用以证明现金出借给于某某的证据。这份证据的时间及金额与苏先生案中的完全一样。这份《借款明细表》中,将借款方式一栏中,现金取款之后标注为“借出现金”,就是说袁某将取出的现金已经出借给了于某某,才能证明她向于某某给付过300余万元的资金。
实则为高利息而现金出借是假
袁某将同一份证据用于两个案件中,涉嫌虚假诉讼,特别是这种行为分别得到了大连二级法院法官的支持。
详细调查袁某提供的现金取款188.8万元的凭证,实则并非都是现金取款,而其中有3笔是转账取款,是将款项通过银行直接转给了第三方的。在查询于某某案卷宗得知,袁某2013年11月11日转账取款10万元换成了欧元、2014年4月10日转账取款54.2万元转到辽阳工行李某名下、2014年4月11日转账取款11.1万元转到辽阳工行张某某名下,这75.3万元并非提取现金,余下的113.5万元提取的现金去向不明。袁某用这种虚假的、瞒天过海的方式来圆自己的谎,更证明了所谓现金出借是假的,是高利息形成。这些观点及证据均在庭审中作过详细的表述,庭后提交过代理词,竟然都被法官有意无意地视而不见。特别是,于某某案和苏先生案的二审审判长为大连市中院同一个法官,同一份证据在两个同类型案件中重复使用,属欺诈行为,法院不仅不追究和排除这种虚假证据,反而在苏先生案判决中主观认定“虽然袁某提供的银行取款记录不能证明所取款项实际交付给苏先生,但其提举该证据的目的是证明其有现金出借的能力,并不能据此认定袁某不存在现金交付的行为。”
在于某某案中已经借出的现金,即袁某手中已经没有这些现金了,在本案中还怎么证明有现金出借的能力;判决中“并不能据此认定袁某不存在现金交付的行为”的判断的依据在哪里呢?袁某没有证据可以证明现金给付的情况下,法院怎么能凭空断定袁某给付现金了呢。
袁某借贷为业反而获得法官支持
从庭审查明的事实可以看出,袁某实际借款本金为136.9万元,苏先生已还款本金数额61.75万元,截止到2015年6月18日,苏先生尚欠本金75.15万元。2016年12月22日苏先生抵顶给袁某房屋两套价值392640元,从2015年6月19日至2016年12月22日,以75.15万元为基数,按年利率24%计算,利息为270540元,即便扣除利息,则仍应相应的扣减本金122100元,则从2016年12月23日起,只欠本金629400元。但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(2018)辽02民终6822号民事判决书却判决苏先生偿还袁某借款本金275万元及自2015年6月19日起的利息按年利率24%计算。这不仅让袁某的高额利息(月息4.5%)合法变为了本金,更将高息继续计算复利。
如此,法官的这份判决简而言之就是纵容违法高利贷的行为。
袁某抵押贷款后再房贷明显违法
经查询大连市房地产交易中心发现,袁某通过原有的三套房屋向银行抵押贷款共364万元,这些款项主要用于放贷,银行贷款有利息,她借给别人的钱能没有利息吗,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。并且袁某2012年10月18日出借给苏先生的70万元是从大连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取得的80万元中的70万元,而袁某在2012年9月28日将自己的房产抵押给农业银行大连西岗支行的债权数额正好是80万元,可以认定该80万元是袁某用自己的房产在银行抵押得来的,并非自有资金,其行为属于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第十四条的情形,是违法的、无效的。
从于某某案到苏先生案,袁某的借贷方式完全一样,包括形成借款合同、借条的格式、标准及方式方法等均一样,连借款形成的结构都何其相似。能查询到的袁某进入诉讼的民间借贷一审案件就有4起,分别是(2016)辽0211民初11975号、(2014)甘民初字第03743号、(2015)甘民初字第00049号、(2011)长民初字第00230号,没查询到的或者没产生纠纷的不知多少。上述袁某的民间借贷行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(2017)最高法民终647号判决书中认定的以借贷为业,借款合同无效的情况,而法院的判决却对案件中存在的诸多虚假的、违法的问题视而不见,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的司法解释、指导意见及公安部和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等部门下发的《关于规范民间借贷行为维护经济金融秩序有关事项的通知》中的精神置若罔闻,违法裁决。
超范围查封严重却没得到纠正
在袁某起诉苏先生民间借贷案中,袁某的诉讼金额为400万元左右,保函金额200万元。然而,大连市中院以苏先生名义被查封的财产却高达2500万元之巨,这在法律及最高法相关指导意见中,完全是违法行为。该案中,袁某的保全金额不足,超保全金额以及诉讼标的严重。如此明睁眼漏的问题均得不到纠正,让苏先生非常怀疑司法的公正性和严肃性。
遗憾的是,对此,苏先生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,并且又向大连市人民检察院申请抗诉,均被拒之门外。法律规定的程序已经走完了,但该案却留下了诸多问题。苏先生认为媒体介入该案并无干扰司法判决的嫌疑,希望有关部门能重视该案,查明事实,纠正错误,使司法公正得以彰显,以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。